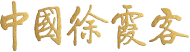张炳德
一
我曾委托上海沈龙法老师找到《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收录到其中对徐霞客作出高度评价的两部分文字:
另一个活跃的领域是地理学。明代出现了大量的县志,最卓越的旅行家是徐霞客,他毕生从事于考察当时实际上还不了解的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他的最大发现是西江和长江的真正发源地,此外,他还发现澜沧江及怒江完全是两条不同的河流。
——《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6年10月第一版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历史概述——全国统一的帝国》第313页
正是在明代,中国出现了一位写游记的名家,即旅行家徐霞客(公元1586-1641年),他既不想做官,也不信宗教,但是对科学和艺术则特别感兴趣。丁文江[ting wen-chiang(3)]曾写过一篇介绍徐霞客的文章。最近张其昀把一些作者写的、专门评论徐霞客的文章汇编成文集。徐霞客在三十多年中曾走遍了全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区,饱尝了种种艰难困苦。他还曾经多次遇到盗匪而被洗劫一空,从而不得不依靠当地学者的资助过活,或者依靠为当地庙宇撰写庙史而得到一些资助。他不论是登上一座名山,或是踏上一条被积雪覆盖的小路,不论是站在四川水稻梯田的旁边,或是走进广西的亚热带丛林,身边老带着一个笔记本。为他写传记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指出,他根本不相信什么风水,而是希望亲自去考察一下从西藏高原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高山地区的情况。他的游记中的精华部分已由丁文江译成英文。(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如梯、坪等,这些专门术语扩大了普通术语的含义。对于每一种东西,他都用步或里把它的大小尺寸仔细地标记出来,而不使用含糊的语句。)
丁文江(他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是中国本世纪颇有科学见解的学者之一)曾举例说明徐霞客所作观察的精确程度。例如,真正的结晶片岩在云南是很稀有的,丁文江本人1914年到云南旅行时,曾在元谋谷底的红色砂岩中看到了典型云母片的露头,并以为这是他的一个新发现。但他后来却发现徐霞客早在三百年前就已经对此作了记载,因为徐霞客在1639年12月6日,就曾经在这个地方看到“其坡突石皆金沙烨烨,如云母堆叠,而黄映有光”。
“徐霞客的主要科学成就有以下三项:第一,他发现广东西江的真正发源地在贵州;第二,他确定了澜沧江和怒江是两条独立的河流;第三,他指出了金沙江只不过是长江的上游;由于金沙江在宁远(即现在的西昌)以南的鲁南山有一个大弯,人们长期没有弄清这一点。”
——《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6年10月第一版第五卷第一分册《地理学和制图》第61—63页。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约瑟这位西方著名的科学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对中国明代徐霞客的科考实践作出了高度评价,肯定了徐霞客伟大的科学精神。李约瑟以一部震动西方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西方科技界介绍了徐霞客及其伟大的游记。中国徐学专家杨文衡教授还写过专论《李约瑟对徐霞客的关注与评价》。
因此,李约瑟工作的英国剑桥大学成了我特别向往的地方,必须实地考察,作一次零距离的接触与感受。
2011年我去英国女儿处度假。出国前徐学界老前辈施光华老先生就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去剑桥大学,找到李约瑟研究所。他并复印了一份他写的《李约瑟的中国情结与鲁桂珍的爱国情怀》送给我,作为背景资料。
二
5月31日我全家5人自驾车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剑桥剑河穿城而得名,为英格兰剑桥郡首府、女王王室领地,离伦敦约90公里,面积40.7平方公里,人口9.79万人。剑桥文明史是从5世纪撒克逊人的集镇开始发展。9世纪为丹麦军事基地,1207年英王在此设郡。
1281年创办剑桥大学第一所学院——圣彼得豪斯学院,市郊也开始有印刷、仪器制造等工业。从此开创了剑桥大学730年的发展历史。1318年,剑桥大学得到罗马教皇二十二世的正式认可,其它学院也纷纷开始创立。当今的剑桥大学是全世界最大、最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大学城”有31个学院、学生16500人,包括5300名研究生,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学生。学校每年招收研究生1600余人、博士生800人、每年授予博士学位700多人。剑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顶级优秀人才到此深造。据统计:剑桥已有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牛顿、达尔文、培根、凯恩斯、弥尔顿、拜伦等著名学者。英国的70位首相以及英国威廉王子也都在此读书毕业。
剑桥大学没有围墙,只有粗大挺拔的百年大树、古朴优美的百年校舍、教堂和学生宿舍。所有学院都保留着一大块绿茵茵的大草坪,各种花卉四季开放。一条康河环绕大学,校舍和教堂依河而建。河道上设多处游船服务站,小河轻舟、杨柳依依,蔷薇等花竞相开放,天鹅野鸭自由戏水。特别是河上那些桥,有历代国王、王后赞美的“叹息桥”、“数学桥”,有我国诗人徐志摩赞美的“康桥”。在三一学院门口有一棵新种的苹果树,是纪念1666年秋天牛顿在此悟到地球引力、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1642-1727),毕业于三一学院,1669年担任剑桥大学教授时年仅27岁。
剑桥大学的确使人神往,它的每项研究成果都迅速传遍世界。
三
李约瑟研究所大门 李约瑟半身塑像
李约瑟研究所大门
李约瑟研究所内 李约瑟故居
李约瑟半身塑像
李约瑟研究所就在剑桥大学。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徐霞客科学精神的研究,就是从此地走向欧洲,传遍全世界的。
李约瑟研究所内鸟鸣声声,花香扑鼻。这是大树掩隐、小桥流水、造型优美别致的二层别墅楼。墙上镶嵌着“八卦图”,东方中国文化的体现使人有为之一振的感觉。研究所门左有李约瑟半身雕像,右墙镶嵌着一块八角形大理石,上面的文字告诉我们:这座研究所,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大使馆在1984年10月20日赞助建立的。
我们按门铃而进,接待人员是一位英国中年学者。我们说明是从中国来,要求参观李约瑟研究所,特别想了解与徐霞客有关的情况。这位英国学者马上用中文说:“徐霞客是中国伟大的地理学家,我们知道。因为有客人来访,不能陪同参观,您们自己参观吧!”
门口的客厅不算太大,挂着在这个研究所工作的学者照片,大多数都是中国的中青年学者。两边走廊挂着李约瑟在中国调研中华科学技术时的照片,其中有他与鲁桂珍以及其他中国友人的合影。走廊里还挂有代表中华文化的绘画、书法以及古代地图。左边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收藏了许多中华文献资料,楼上也均是中文图书,这在英国是很少见的。我看了英国的书店,基本没有看到过中文的图书。右边的过道和二层大部分是办公室,有许多学者在工作。整个研究所中国文化元素相当多。
李约瑟研究所内
李约瑟故居
我翻了一下来访人员的签名簿,几乎每天有人来参观。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人士也不少,大都是奔着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来的,对李约瑟和鲁桂珍充满了敬仰和感激。
有位刚来一个月的研究员对我们说:园内那边二层的小平楼就是李约瑟的住房,现在已出租给别人居住了。小平楼门前一片绿茵草地,房后是参天大树郁郁葱葱,一座刻有“云岫”汉字的太湖石矗立在树丛中。就在这幢极普通的二层平楼里,李约瑟用心编写出了整套几千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巨著。他用西方人的科学观和方法来研究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科学技术发明和使用实践(理论),以极为充实的证据,说明了当代世界中国科学技术正在发展,走在世界前列。徐霞客的科学精神和《徐霞客游记》都被他列入这部巨著中,向西方、向全世界宣传徐霞客科学精神对人类的贡献。
李约瑟研究所,的确是一座中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
四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横空出世,是由李约瑟和鲁桂珍为代表的英中学术合作的典范。
李约瑟(1900-1995)英国人,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医学之家。他的父亲是解剖学教授、病理组织学者及著名的麻醉学家,母亲是个颇有成就的音乐教师和作曲家。1918年他进入剑桥维尔斯学院,192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24年获哲学和科学博士。1931年到1942年他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及《生物化学形态发育学》两部巨著,使他成为著名的生物化学和胚胎学家,又使他历任剑桥岡菲—克兹学院的院长和校长等职。
鲁桂珍(1904-1991)出生于中国南京市太平路249号一个中医世家。祖籍湖北蕲州,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产生地。她的父亲鲁茂庭是思想开明、医术高超的中医,母亲陈秀英知书达理。鲁桂珍从小就受到中医学的熏陶,父亲鲁茂庭对她说:“不管欧洲人对中国古代科学如何生疑,总有一天要承认这一切的。”她始终不忘中医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为日后与李约瑟合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第5、6卷打下了基础。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鲁桂珍与王应睐、沈诗章等人远渡重洋,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她进了李约瑟夫人李大斐的研究室进修,并与他们夫妻成为亲密朋友。从此,鲁桂珍便与李约瑟这位有哲学头脑、精通法、德、俄、拉丁、希腊文,并且十分熟悉希腊、罗马以及欧洲科学历史的科学家一起,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进行认真交流。鲁桂珍耐心教李约瑟识汉字、读汉文,为李约瑟在中国抗战时期来华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打下了基础。他们在美国工作和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时,都讨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课题,相约今后在剑桥大学全面展开实施方案。1948年,鲁桂珍到巴黎和李约瑟夫妻共事,再一次讨论中国科技史的课题,并推动李约瑟辞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回到剑桥专心致志从事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李约瑟与当时在剑桥的中国学者王玲合作9年,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言和第二卷、第三卷的有关篇章。这时的李约瑟想起给他合作力量的鲁桂珍,以及她父亲鲁茂庭的话。于是在1954年,该书第一卷在剑桥大学出版时,他在书中深情写道:“我把本书的第一卷献给鲁茂庭先生,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任何一个单独的欧洲人或中国人都是难以完成的。
1957年,王玲赴澳大利亚任教,李约瑟向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鲁桂珍发出邀请,希望能与她合作,把刚刚启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继续编下去。鲁桂珍听取了好友郭沫若先生转达周恩来总理的话:“你如果要回国,就做好准备。但是在英国,这项工作更有意义。没有您,这项工作恐怕不能继续,还是留在先生身边吧!”她义无反顾地辞去了联合国的工作,回到剑桥。她热爱祖国文化遗产,无私奉献的精神,再一次征服了李约瑟,开始了他们长达30年的合作,去完成这一丰碑之作。李约瑟具有丰富的欧洲科学技术知识,并且刻苦钻研,注重调查,实践掌握第一手资料,又有鲁桂珍深厚的传统中华文化和研究传统中国科学技术的信心。他们俩先后8次到中国,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加上国际上各方面的协助,最终英中合作有了伟大的成果。
李大斐去世后两年,李约瑟和他志同道合的战友鲁桂珍于1989年结为夫妻。1991年,鲁桂珍因患气管肺炎而去世,享年87岁。4年后,李约瑟也与世长辞,享年95岁。
现在,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已出版18册,预计全部文字将超过4500万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已经享誉全世界,使他们成为了中国科技史的权威大师。在其影响下,中国科技史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世界性科研课题,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
李约瑟和鲁桂珍,堪称英中学术合作的典范
李约瑟是一个西方人,对东方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他用“愚公精神”来发掘中国几千年瀚如烟海的科学发展史,用西方人的科学观念来评价和证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中国“奇人”徐霞客科学精神的理解和高度评价贡献给全人类,这就是科学的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作者系江苏省徐霞客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