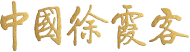在游记的绿地上,建构宏伟的散文大厦
——《徐霞客游记》文学论之二
蔡 崇 武
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与之相应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作为中国游记文学的一座高峰——《徐霞客游记》问世后,许多专家、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到这个问题。著名学者钱谦益称其为“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真、大、奇三个字,不仅从内容上对《徐霞客游记》作出了高度评价,而且对其文学体式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朱东润先生也关注到了这一点,他在《〈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一文中指出:“这样的写法,是前人所没有的,……在游记之中,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但这是怎样一条新的出路,他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梅新林、俞樟华在《中国游记文学史》中,恰好补充解读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徐霞客游记》象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一样,是对郦道元《水经注》所创造的“一种综合型游记新范型”的继承。这种综合型游记新范型的特点的是,融科学考察、史地辨证、山水描摹、风情笔录、古迹考证等于一炉。著名的地理学家、徐学研究专家丁文江先生,则以严谨的科学的眼光,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观志目知先生之志,纯系创作,与其他山志迥异。”这里的“创作”,实际上是指创造与创新,当然丁文江先生绝不是否认文学的继承关系。他只是强调了《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创新之作。由此可见,众多专家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徐霞客与以往的山水游记作者截然不同,他的游记别开新界,创造了一种游记写作的新范型、新体式。这种新范型、新体式,由于当时的散文分类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细化,大家只是敏锐地感觉到了,但无法给以确切地判别。其实,徐霞客所创造的这种文学新范型、新体式,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游记大散文。正是这种大散文的新范型、新体式,成就了徐霞客百科全书式的游记,并把他推上了晚明游记文学的高峰。
那么,徐霞客是怎样在继承古代游记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建构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游记大散文的呢?
一
中国的散文历来讲究“形散神不散”。1961年《人民日报》萧云儒在“笔谈散文”栏目中,发表了《形散神不散》的短论后,得到广大文艺理论家与散文作家的赞同。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是什么创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歌咏声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征圣”篇中,也有过论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意思说:“思想深刻而语言漂亮,感情真实而辞句巧妙”,并强调说,这是写文章的全科玉律。这里的思想和感情,就是指一篇文章的“神”。这种“神”,就是文章的灵魂。试想一下,一篇散文没有这样的不散之“神”,没有灵魂,文章何以能成功建构,又怎能去感动读者呢?一篇短小的散文尚且如此,那么,大散文呢?大散文由于篇幅较长,没有不散之“神”加以贯串,大散文创作,将是一盘散沙,绝对不会成功的!
《徐霞客游记》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游记的每一篇,乃至洋洋六十余万字的整个游记中,始终凝聚着一个不散之“神”,那就是徐霞客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艰险,“问奇于名山大川”的执着追求精神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精神。正因为这样,这一游记大散文有了灵魂,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作品蕴藏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处处闪耀着高尚的人性之光。
我们知道,《徐霞客游记》有别于当时风行的明人小品,他采用了日记体记载了“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经历。日记体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活泼,可以随时抒写个人的主体情感,真实地记录自己的亲历亲为。他正是利用了日记体这一文学样式的优点,巧妙地从不同的侧面,把这一不散之“神”,贯串到整个游记之中。
一是在记游中不时挥入表述自己志向的文字,从而向读者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文人雅士的即兴而游,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文化考察之旅。如《游嵩山日记》一开头,就这样写道:“余髫年蓄五岳志,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又如《游九鲤湖日记》中这样表述:“余志在蜀之峨嵋,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若罗浮,衡岳次也;至越之五泄,又次也”。这些记述,充分说明徐霞客的行游,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即使临时改道,也都是蓄志已久,如《滇游日记十三》中有这样一段记叙:“初九日,霁甚。晨饭,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苍山,洱海之兴。”这表明,苍山、洱海早就是他决定考察的对象。这些文字,不是作者有意的自我张扬,而是信手拈来,十分自然真切,然而,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叙述,使作者“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理想之光,穿透了整个游记。
二是作者在游记中,真实地记述了旅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有的时候,甚至命悬一线。如《楚游日记》中,作者游麻叶洞时,游记中如是记载:“既逾洞左急流,即当伏水而入,道者只供炬艹热火,无肯为前驱者。余乃解衣伏水,蛇行以进,石隙既低而復隘,且水没其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火炬,平出水上,乃得入”。又如《游黄山日记》中,作者雪后登光明顶、石笋矼时,因雪后石级被积雪掩埋,无路可登攀,只能凿雪而上:“数里,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请想一想,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更不要说,当时社会的治安状况不好,时有盗贼出没,兵燹之灾呢。这些真实的描述,使徐霞客矢志不渝,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精神,在游记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三是通过一些典型事例,突出了徐霞客的高尚的品格和对朋友,对贫苦者的博爱精神。这里最突出的就是游记中对徐霞客与静闻的深厚情谊的描写。当他听到顾仆说,静闻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尸骨葬于鸡足山后,他念念不忘,准备亲自把静闻的遗骨带往鸡足山。但当他再次来到静闻寄骨的南宁崇善寺时,遭到了宝檀、云白两个和尚的勒索、刁难,为此,他毅然放弃索取静闻留下的钱物,“止索戒衣、册叶,竹撞,其他可易价者,悉不问”,从而求得云白和尚的同意,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取出静闻的遗骨,然后亲自把它装入骨瓶,带到鸡足山安装,了却了静闻的遗愿。这种重情义、守承诺的传奇式的壮举,叫人读了谁能不为之动容?另外,游记中还真实记载了其他一些事例,无不带上他独特的人性光芒,如《黔游日记一》中,记载了一个无赖王贵,他几次三番欺骗徐霞客,然而,徐霞客仍是“余纳而憐之,途中即以供应共给之”;等到游南山再次碰到王贵,徐霞客不计较王贵不辞而别之前嫌,而是继续收用他,并给他“每日工价予一分,若遇负担处,每日与工价三分半”。乃至麻哈,王贵“逐渐傲慢,以凳伤予足”,徐霞客仍然“复用之”,直到王贵偷了他的钱,逃之夭夭,他只是感叹“蛮烟虺毒”之烈,也没有去追究王贵。这充分说明,徐霞客心胸之宽广,对贫苦者有着深厚的同情之心。
此外,游记中处处突现了他坚持真理,不懈求索的精神。这样的例子,在游记中比比皆是。例如在《游雁岩山日记(浙江温州府)》一篇中,当他决定去山顶寻觅雁湖时发现:“已而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又石片稜稜怒起,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这时他对志书中记载的:“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发生了怀疑,并根据自己的考察,作出否定性的结论:“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这虽然是个小小的细节,但徐霞客也没放过。就这样,徐霞客通过这些多侧面的记述。让这一不散之“神”——徐霞客精神,贯串到了整个游记中。而游记中的每一篇日记,正因为有这样的不散之“神”,顿时有了生气,象一粒粒闪光的珍珠,被串连了起来,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二
中国的游记文学,是随着文学散文一起,在魏晋时代同时诞生的。由于文学散文与古代的书、诗、赋、序等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因此,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精短简洁,清新华丽“以情披文”。但游记大散文不是这样,它是钱谦益所说的“大文字”。《中国游记文学史》作了进一步的解析:“所谓‘大文字’,即大容量、大气象,具体来说大致表现在内容的博大和景象的大气上”。当然,他们只是从内容上概括了“大文字”的特点,其实,与此相应的文学体式上,也有其特点,那就是体制宏伟、篇幅较长、独自成篇,我认为,这才是游记大散文区别一般的文学散文,或者说常规的游记散文的基本特征。那么《徐霞客游记》又是怎样体现大散文这一基本特征的呢?
我们不妨把《徐霞客游记》逐篇作一剖析,就可以发现,除去《盘江考》、《溯江纪源》和《滇游日记一》中两则单篇游记外,其余三十八篇都是大容量、大气象而且体制宏伟,篇幅较长的游记大散文。在这三十八篇游记中《游白岳山日记》和《游黄山日记续》相对简短些,其余都在三、四千字以上,一般都在万余字,甚至几万字以上。当然《盘江考》、《溯江纪源》等也须臾不能忽视,因为它们是“游记大散文外的专记,是游记的补充及延伸。
综观这些游记大散文,都具备下列几个特点:
一是容量大,气势恢宏。每一篇游记都包含了山水风光、社会风情、古迹考证,科学考察等内容,体现了大散文的特有的综合性与包容性。如篇幅不算太长的《闽游日记前》,从三月十一日江山之青湖,登上入闽之道起,一直到四月五日访其叔官漳州司理者于南靖为止,这短短的二十多天中,游记就记述了徐霞客所经过的仙霞嶺、丹枫嶺、仙阳嶺、蒲城、永安、建宁、顺昌、将乐、漳平、华封、漳州等地的沿途风光,其中还真实地插入了“闽中以雪为奇”的民俗风情的描写。对途中的重点胜景——玉华洞进行了详细考察。最为可贵的是徐霞客在漳平时,对建溪与沙溪的源流及入海流程进行了科学的考证,从而得出了“建、沙二溪之夷峻相较,而知两嶺之高相等,而马嶺至海近,黎嶺至海远,故宁洋溪流急于建溪”的结论,这一发现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它揭示了水的流速与水的流程相关性的原理。在一篇文章中能涵盖这么多内容,这在一般的文学散文中是完全不可能的。《闽游日记前》是如此,那些比《闽游日记前》长的游记,更是容量博大,气势宏伟,读来让人震撼。
二是游记大散文虽然容量大,气象万千,但它的散文的各种元素俱备,不仅没有削弱其文学性,相反更加色彩斑斓。如《楚游日记》中,徐霞客来到一个叫“五雷池”的地方,对美不胜收的雪景,作了如下描述:“而庵中山环水夹,竹树蒙茸,萦雾成冰,玲珑满树,如琼花瑶谷,朔风摇之,如步摇玉珮,声叶金石。偶振堕地,如玉山之颓,有积高二、三尺者,途为之阻,闻其上登陟更难”。这里,作者没有刻意地用华丽的词藻去铺叙、描摹,他只是对途中所见所感,信手写来,但让我们读了,如亲历其境,产生无限的美感,特别是诗一般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比喻,超现实的想象,使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文学修养之深厚!象这样的文字,在游记中几乎俯拾皆是。如在《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中,徐霞客所写的“龙鼻水”的景象:“龙鼻之穴,从石罅直上,似灵峰洞而小,穴内白色俱黄紫,独罅口石纹一缕,青绀润泽,颇有鳞爪之状,自顶贯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内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只寥寥数语,就把“龙鼻水”之逼真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游记大散文,不管它规制有多宏伟,篇幅有多长,它始终是散文百花园中一株不可分割,然而又是同类异构的奇葩。
三是游记大散文为了适应其内容之博大的需要,其文章篇幅都比较长,框架都比较大。为了建构这样的大散文,徐霞客在游记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章结构方式,那就是围绕一个旅游考察对象,以足迹为线索,排日记事,然后按旅游考察对象,考察的起始与结束的日期,排成一个“时段”,再利用这一完整时段内的日记,单独组合成篇。简言之,就是“对象统一,排日记事,时段立篇。”我们可以从相对单一的名山游记入手,作一个简单的剖析。如《游黄山日记(徽州府)》,这是徐霞客在三十一岁时,与浔阳叔翁一同前往游览与考察的。时间是1616年阴历二月初二至二月十一日,共计10天。这10天中,每天都有日记,日记的主要内容,都围绕着一点而展开,那就是“游黄山”,正因为这样,这10天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时段。这10天前虽然徐霞客也在徽州府,但他在游白岳山,与游黄山无关,二月十一日后,则去福建游武彝山了。因此游黄山的日记,虽然单独“排日记事”,但日记的内容则是相互衔接的,如果去掉日期,实际上就是单独成篇的《游黄山记》。因此,把这10篇日记,组合成一篇游记,既合乎当时的实际,又使独立分散的日记联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建构了一篇游记大散文。这种建构游记的方法,对于一山一水的游览与考察,容易理解,特别是游记中前十七篇,几乎都是这样建构而成。但在《徐霞客游记》中,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从第十八篇开始,徐霞客改为以一个“地域”作为综合游览与考察的对象,这些游记大散文又是怎样建构的呢?我认为,基本方法还是“对象统一,排日记事,时段立篇”,特别是《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与前边十七篇名山游记如出一辙,只是规制更宏伟,篇幅更长大,记述的内容更丰富而已。如《浙游日记》就是集中了徐霞客“丙子(1636年)九月十九日自家起身,由锡邑、姑苏、昆山、青浦至浙江杭州,历余杭、临安、桐庐、金华、兰溪、西安、衢州、常山诸郡县”的28天的日记(见《徐霞客游记》校勘记),而整篇游记就是这28天为一个时段组合而成的。到《粤西游日记》开始,游记建构的方法又有了些新的变化,同一篇大散文分成了若干个片断,编排成日记一、日记二、日记三、日记四等等,如《滇游日记》分成了十三则日记。但我认为,不管分成多少则日记,这只是《徐霞客游记》整理者、编辑者考虑到这些游记大散文,规制太庞大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而人为的分隔处理。每一个“地域”游记,实际上还是遵循着“对象统一,排日记事,时段立篇”的原则在进行,只是把原来几个月,甚至一、二年中若干个小时段,合成了一个大时段而已,而一个大时段内形成的日记,还是相互衔接,构成了一篇规制特别宏伟的大散文,如《粤西游日记》,尽管分成了四则日记,但总的仍然是一篇独立的游记大散文,它就叫《粤西游日记》。这里,最好的证据,就是分成日记一、日记二的《黔游日记》,据该篇游记的《校勘记》注释:“黔游日记,徐本在第六册,题曰‘黔’,不分一、二”。这充分说明《徐霞客游记》按地域记游的日记,原来就是个整体,不管它是几千字,甚至几万字,那怕十几万字,它是不可分割的单独成篇的游记大散文。
三
大散文与一般的文学散文之区别,不仅仅在于篇幅上的长大,气象上的恢宏,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显现出来的特有的文化属性。大散文注重于历史的反思和文化的批判,这是建构大散文的核心要素。这里的历史的反思和文化的批判,不能简单地、机械地把它割裂起来理解,而是指大散文中必然对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社会事件或现象,从文化层面上给予解读和批评。从而使作品保持着历史的沉重感,同时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徐霞客充分关注到了这一点,他凭借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厚的文学修养,在这方面作出了独特的探索,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集中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徐霞客摈弃仕途、寄情山水,以自身的实践,张扬对时代的叛逆。徐霞客出身于“南州高士”家庭,“据《后汉书》所载,被称谓南州高士者是江西南昌人徐稚,他生于恒帝之世,面对朝政腐败,宦官专权,正直放废,便决心隐迹山林,过耕读生活。”(见薛仲良《徐霞客家集》)。徐稚为徐霞客的祖辈。徐稚之后,被称为“梧塍徐氏一世组的徐锢,四世祖徐守诚,五世祖千十一,皆继承了徐稚的“高士遗风”。九世祖徐麒,虽然白衣应诏,出使西蜀,招抚羌人,立功异域,但当功成名退后,仍稳居梧塍。到了徐麒的长子徐景南的时代,因其出谷赈灾,出鞍马助边等义举,被明王朝旌为“义民”。于是他萌发了追求功名利禄、报效朝廷的思想,从此,徐家开始了五代人的科场角逐。然而,由于社会的腐败、科场的黑暗,均未取得成功,有的甚至招致牢狱之灾。生长在这样家庭中的徐霞客,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承祖上的“南州高士遗风”,避世隐居;要么象前几代祖辈一样去追求功名利禄,逐鹿科场。但徐霞客最后两者都未选择,而是在晚明“实学”思潮的影响下,走上了一条“寄情山水”,开展旅游考察之路。因此,徐霞客的选择,实际上是他对朝廷科举之弊和家族历史的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当时时代的一种叛逆。洋洋六十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就是他寄情山水,开展旅游考察的实录,整部游记也就成了他叛逆时代的最有力的佐证。在游记的不少篇章中,也时时显露出他这种叛逆精神的光芒。如在《浙游日记》中,有一段记载他在金星峰头月光下的独特感受的文字,极其发人深思:“夕阳已坠,皓魄继辉,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另一是静闻)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嘶啸、酾酒临江,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经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这一段文字,表述了徐霞客脱离尘世,独游万山之巅,达到了形神合一,天人相应的境界,因此“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这种境界,表明了他摈弃科场,寄情山水的无怨无悔,同时也表达了他决不与世俗合流,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的决心。因此,钱谦益称徐霞客为“千古奇人”,其实,徐霞客之“奇”,就奇在这一对时代的可贵的叛逆上,“千古奇人”的评价,真是名至实归。
二是徐霞客在游记中,对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社会现象,能从文化的层面上,给予深刻地解读与判析。徐霞客在西游途中,经常来回于中国的边界上,因此,有较多篇章记述了国家的边患问题。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先是用较多笔墨揭露了当地州府官员勾结异族,争权夺利,相互掠杀的历史真相,然后用其独到的观点,对这种勾结异族、出卖国家利益的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揭露了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真正原因。在《黔游日记一》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沙营东北为郎岱土酋,东北与水西接界,与安孽表里为乱,攻掠邻境,上官惟加衔饵,不敢一问也。”这充分说明,严重的边患,上级官府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放任自流,“惟加衔饵”,从而使得边疆无一日安宁,边患越来越严重。那么,州府官员为何敢如此恣意妄为呢?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三》的一条夹注中,把矛头直指当朝执政者:“当道亦有时差官往语莫酋者,彼则厚赂之,回报云:彼以仇閧,无关中国事。岂踞地不吐,狎主齐盟,尚云与中国无与乎?”很显然,问题的根子还是当朝者昏庸无能,那些差官,受了异族的贿赂,竟然以谎言欺骗朝廷,朝廷亦不追究。因此徐霞客愤慨之极,发出了“岂踞地不吐,狎主齐盟,尚云与中国无与乎?”的严厉斥责。徐霞客这种坚持正义,敢于直面批评当朝执政者的大无畏精神,不仅为我们全面理解徐霞客精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为游记这一“千古奇书”增加了浓重的时代色彩。
此外,徐霞客在游记中,多方面对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如《粤西游日记二》,记载了徐霞客亲见的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夜半,复有探者扣扉,入与主人宿,言麻兵者,即土司汛守之兵,夙皆与贼相熟,今奉调而至,辄先与二骑往探,私语之曰:‘今大兵已至,汝早为计’。故群贼縻遵者一人斩之,以首级畀麻兵为功,而贼俱夜走入山,遂以‘荡平’入报”。这里,揭露了兵匪一家,通风报信,假斩一人,放走盗匪的真相。又如,徐霞客在粤西游途中,因雨投宿于“勾漏庵”中,老道外出未归,老道去了哪里,文中作了交代:“既而雨止,时已暮,道人始归。乃县令摄以当道,欲索洞中遗丹及仙人米,故勾摄而去”。请看,作为一县的父母官,连一个道士也不放过,竟然向他勒索“洞中遗丹及仙人米”。这里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但对当时社会之黑暗,官府之腐败,真是揭露得入木三分。
我们知道,晚明时期,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在当时大批文人,在写作小品式的“才人游记”,专事抒写个人性灵之际,徐霞客能关注国计民生,抒发其忧国忧民之情,并以其独到的见解,对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现象作出深入的剖析,这不仅把他的游记提升到了一定的历史的高度,而且充分彰显了他的游记大散文的文化属性,这一点在中国游记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肯定。
三是徐霞客不迷信权威,在旅游的过程中对所见所闻,始终以科学的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重新审视。这里,对徐霞客在旅游考察途中,在科学上的发现及取得的成就,许多徐学专家早已有了定论,不少人因此把游记称之为“科学考察游记”。但我认为,徐霞客毕生“问奇于名山大川”,从文学的层面上来看,实际上他是一次对祖国名山大川及有关地域的文化考察之旅,而不是纯粹的科学考察之旅。他许多新的科学发现,只是他在文化之旅的过程中,对新奇见闻的记载;而对某些经典著作中错误的纠正,那是他文化之旅的过程中,科学思维的结果。这最突出的就是纠正《禹贡》中的“岷山导江”之说。这本身就是一次文化实践。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徐霞客游记》科学上的成就,而否定其文学上的光辉。实际上,从广义上来看,文化考察之旅,包容了科学考察之旅,两者是一致的,不矛盾的。在这部巨著中,文学性与科学性是交叉融合的。在有的篇章中,文学性还比科学性显得更为突出、鲜明。我们只要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就可以发现,他对山水名胜、文物古迹的鉴赏及考证,远远多于科学的考察,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纠正方志和民间传说的错误,这几乎遍及各个游记。如《粤西游日记二》,共有日记七十一篇,在这七十多天中徐霞客游历了数十处名胜古迹,其中八处提出了质疑。如在丁丑(1637)六月十六日,他过唐二贤祠,发现由其内西转为柳侯庙,庙后还有“柳墓”,这时他就用专条提出疑问:“余按一统志,柳州止有刘蕡墓而不及子厚,何也?容考之。”但他没有立即否定,而是“容考之”,说明其科学态度之严谨。又如在七月二十三日,他参观大寺圆珠池时,联想到《西事珥》和《百粤风土记》中有山北漱玉泉“暮闻钟鼓则沸溢而起”的传说,他经过实地考察后,给予纠正:“余谓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侯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而为沸寂也。”这种解释,就显得科学合理。因此,这种文化的批判精神,正是《徐霞客游记》这一大散文的亮点。没有这种文化的批判精神,无论是文学还是科学,都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当然,大散文的概念才提出不久,其理论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但我坚信,《徐霞客游记》作为中国第一部游记大散文的代表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它一定会列入我国文学经典名著之林!
2014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