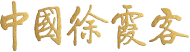

夏树芳,他说徐母王孺人出生于江阴
蔡崇武
唐汉章先生在《徐学研究》(2022/3总第六十三期)上发表的《求证务实,去伪存真——徐母王孺人籍贯考》一文,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徐母王孺人为江阴人。文章集中火力驳斥了无锡某些人对陈仁锡原文“城东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的歪曲与攻击,还了陈仁锡清白。同时,还列举了高攀龙、林釬、夏树芳等人在徐母王孺人八十大寿之际作有诗文盛赞王孺人,而且用多种方式指出王孺人为江阴人。因为我正在研究古代江阴人与徐霞客之间的关系,所以作为江阴人的夏树芳引起了我的关注。唐汉章先生这样写道:
夏树芳《秋圃晨机图赋》:“维坤元之表粹,毓女德之清芬。演仙胄于瑶池,度灵纪于西昆。婺星散彩,诞我江濆。既淑且嫕,亦和而贞。适东海之名阀,配南州之喆人。……”夏树芳(1551—1635),字茂卿,号冰莲居士,江阴人。万历乙酉(1585)举人。侍母孝,隐居江阴长寿、云亭二镇交汇的毘山东麓能仁寺数十年。万历间辑《法喜志》,有著述多部。崇祯元年,作《忠尽篇》追悼东林党诏狱死难诸人。另著有《消暍集》传世。“诞我江濆”句分解:“诞”即诞生之意,“我”当泛指我们江阴,“江”即指江阴,而“濆”泛指水边,江阴在长江之滨,故“江濆”一词亦泛指江阴。……“诞我江濆”句即意为徐母王孺人诞生在我江阴。她嫁给了谁?夏树芳也说得很明白:“适东海之名阀,配南州之喆人。”“适”与“配”都是嫁的意思。宗谱中涉及女儿嫁给了谁,一般都用适某某,配字就更好理解,即嫁配的意思。“名阀”、“喆人”都是对江阴梧塍徐氏家族的尊称。夏树芳以满腔热情赞美徐母王孺人,字里行间充满江阴人的骄傲与自豪。
唐先生此段关于王孺人出生于江阴的记述,十分清晰、详实,读来令人十分感佩。笔者正是在其论述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新的探索,有了一些新的体会。这些体会也许对进一步理解唐先生这一重大发现,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是夏树芳这样为王孺人祝寿,是徐霞客亲自上门拜访的结果。夏树芳在《秋圃晨机图赋》序言中写道:“王母徐太君《秋圃晨机图》,梁溪陈伯符写照,吴中张灵石布景。一时诸名公若李本宁、董玄宰、陈仲醇一一品题其上。仲子弘祖挟册自梧塍来,乞予为赋。予喜而为文以赠之。弘祖雅好游,海内佳山水,二十年来,足迹几遍天下,盖也当世一奇男子也,因纪母氏之徽音,遂乃及厥子云。”当时的夏树芳,正如唐汉章先生所介绍,他“隐居江阴长寿、云亭二镇交汇的毘山东麓能仁寺数十年”。他之所以隐居毘山,因为他是个孝子,主要服侍母亲。当然,他知道徐霞客也是个孝子,因此,当徐霞客上门为母亲求祝寿词时,他欣然同意。从序言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徐霞客也非常重视这次为母亲求祝寿词的拜访,他不仅提供了《秋圃晨机图》的拓本,还亲自“挟册”前往,详细地向夏树芳介绍了母亲王孺人的情况。在介绍中,肯定告诉了夏树芳,母亲为江阴本地人。夏树芳长期隐居在山区,对远在几十里开外的徐母估计不会了解,王孺人的所有情况,应该都是徐霞客提供的。更为重要的是,据《徐霞客游记》记载,所有纪念王孺人八十大寿的文章,在收入晴山堂石刻时,都一一经过徐霞客的校核。这有力地证明,夏树芳在祝寿词中写的“婺星散彩,诞我江濆”等内容,徐霞客均是知情并赞同的,由此可以有力地证明,徐母王孺人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江阴人。
这段序言中,夏树芳还写到了“梁溪陈伯符”,由此可知,夏氏的诗文交代明白,“毫不含糊”,“江濆”就是江濆,“梁溪”就是梁溪,假如依现在无锡某些人所说,王孺人就是无锡人,夏氏大可就直接写作“诞于梁溪”了。事属细节,交代明白,史实凿凿。
二是夏树芳在《秋圃晨机图赋》中,对王孺人从出生到结婚作了完整记述。他写道:“婺星散彩,诞我江濆。既淑且嫕,亦和而贞。适东海之名阀,配南州之喆人。”这里不仅交代了王孺人“诞我江濆”即出生在我江阴,而且对其为人高度赞赏,说她“既淑且嫕,亦和而贞”,意思是她的为人既贤淑又文雅,性格和善而注重贞节。到了婚嫁的年龄,“适东海之名阀,配南州之喆人”。这里的“东海”借指江阴,“名阀”意为名门豪族,“南州”指徐霞客家祖上是东汉隐士、时称“南州高士”徐穉后裔,“喆人”指智慧聪明、卓而不凡之人。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它描述了王孺人从出生到结婚的经历,不仅证明了王孺人为土生土长的江阴人,而且嫁了一个好人家,就是江阴闻名的徐家。这在所有为王孺人八十寿庆的祝词中,是唯一的一篇详细记述其从出生到出嫁的祝词。毫无疑问,这都是听徐霞客介绍的,真实性绝对可靠。不仅如此,还详细地描写了王孺人耕织生活,写她“春园不涉,秋圃治蔬”,“豆花棚下,插架编蒲”,“晨鸡乍唱,晓钟初歇,札札兮杼韵之动微风,轧轧兮机声之落残月”。织出来的布,“一纬一经,若抽若曳,皎洁兮若天半之飞霜,皑白兮若倾筐之积雪”。面对这样劳苦的耕作生活,作者感慨地道:“盖白叠黄筒,初非农圃之所尚,而纬车课绩,实太君之所为朝夕而勤劬。”作者在这里,说出了王孺人对劳动之热爱,她视为这是一种应该作出的奉献。由此可见,王孺人有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因此,董其昌,陈继儒在王孺人去世后的悼词中称她为“布衣”,即平民,实在是十分恰切的,连徐霞客看了也默认赞同。因此,夏树芳笔下的王孺人,生于江阴,嫁于江阴,一生劳作于江阴,是个顶天立地的江阴人,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三是夏树芳这份贺词的写作时间,是在徐母王孺人八十大寿期间,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比陈仁锡写的《王孺人墓志铭》早了一年。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写道:“天启四年,甲子(一六二四)。先生年三十九岁。是年先生母王孺人八十。”夏树芳就在这一年为徐母王孺人写了祝寿词。而后,丁文江先生在《年谱》中又写道:“天启五年,乙丑(一六二五)。先生年四十岁。九月,先生母王孺人卒。”陈仁锡就在这一年,为徐母王孺人写了《墓志铭》。为什么在关注夏树芳为徐母王孺人写祝寿词时又提陈仁锡为徐母王孺人写的《墓志铭》?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虽然两篇文章,一是祝寿词,王孺人尚在人世;一是《墓志铭》,王儒人已经逝世,但两篇文章中,都对王孺人的生平作了叙述,都提到了王孺人出生于江阴。这一点特别重要,是证明王孺人为江阴人的历史证据。二是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写作上的时间差异,而且记载王孺人生于江阴时,表述上各不相同,一说是“江濆”,一说是“澄江”,而“江濆”也好,“澄江”也好,都是指江阴,这充分证明写作上,两者有着各自的独立性,表明了文章所述内容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三是作为物证来看,两个证据比一个证据更有力。在法律上,两个以上的证据比起孤证,更容易作出正确的最终判断。四是《秋圃晨机图》是“仲子弘租挟册自梧塍来,乞予为赋”,就说此“赋”是徐霞客亲自上门恳求夏氏撰写的,是徐霞客亲历所为。“诞我江濆”是得到徐霞客充分认可的,假如如无锡某些人所说王孺人是无锡人,徐霞客又何不请夏氏改成“诞于梁溪”,而让“诞我江濆”一说流传至今呢?
近几年来,对于徐母王孺人的籍贯问题,原先以为只有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提及,因此,无锡某些人为了在无锡建造贤母祠,就胡说王孺人不是江阴人,而是无锡嘉乐堂人。为了寻找理由,硬说陈仁锡是“一时趁笔”,搞错了,于是对陈仁锡进行无情的嘲讽。面对夏树芳文章中的新证据,无锡某些人是不是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是否还值得为那个虚构的嘉乐堂王孺人继续鼓噪?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汉章先生的这一发现,不仅宣告了无锡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是十足的冒牌货,而且这一发现,在徐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值得我们向一贯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工作在徐学研究一线的唐汉章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系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