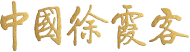中国古代自然文学的一座丰碑
——《徐霞客游记》文本性质之考辩
蔡崇武
《徐霞客游记》(下简称《游记》),自季梦良于壬午年(明·崇祯15年,1642)整理完稿并正式出版以来,至今已有378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游记》文本性质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过。那么,究竟给《游记》如何定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
关于《游记》文本性质的争论,是从1927年7月,著名的地理学家丁文江先生编纂、整理的《徐霞客游记》出版后开始的。之前的280多年中,众多著名学者都认为《游记》是文学游记。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钱谦益肯定《游记》是“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是千古奇书。到了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收录了它,虽然由于《四库全书》体例的限制,把它收录入“地理类”,但仍没有否认《游记》的文学性,赞扬其为“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但丁文江先生不这么认为,他在自己新编的《游记》序言中,称《游记》为“舆地之学”,认为《游记》是地理学著作,属于科学著作。从此揭开了《游记》是文学著作,还是科学著作之争。到了1941年的“纪念徐霞客逝世300周年大会”上,丁文江的观点,得到了与会科学家的热烈响应。尽管著名的地理学家,复旦大学的教授谭其骧据理力争,坚持说《游记》是文学著作,但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到了1958年1月28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说:“《游记》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而且他用了个递进复句,强调了《游记》文学性是第一位的,从此,《游记》的性质,得到了明确的肯定。但是对《游记》文本性质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息。1980年,褚绍唐、吴应寿先生编辑的《徐霞客游记》正式出版,他们在《游记》的序言中说:“《游记》既是科学著作,也是部名副其实的文学游记。”他们在科学著作与文学著作的关系上,用了并列复句来提示,显然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有明显的差异。十年后,朱惠荣先生的《徐霞客游记全译》出版,他在《游记》的前言中对《游记》作了多元化的定义,说《游记》不仅是“导游手册”,还是“地学百科全书”、“历史实录”和“文学游记”。这是回避“科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的巧妙的处置,但他所强调的四个说明《游记》的特色属性,实际上也是并列关系,这说明他是赞同褚绍唐和吴应寿先生的观点的。到目前为止,应该就整个徐学界对《游记》文本的性质,实际上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大致有四种意见:一是沿袭传统的看法,认为《游记》是文学著作;二是以丁文江先生为首,认为《游记》是科学著作;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认为《游记》有双重属性,“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强调《游记》的文学属性是第一位的;四是以褚绍唐、吴应寿(包括朱惠荣先生)为代表,认为《游记》既是科学著作,也是文学游记,两者是并列关系。因此,近百年来,对《游记》的文体的定位,一直处于探讨与争论中,未能形成共识。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游记》文本性质的争论中,我也积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毛泽东关于徐霞客及其游记的伟大论断》和《<徐霞客游记>文本性质历史解读与辨正》两篇文章中,我表明了自己赞赏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认为《游记》实际上是一部长篇的散文著作,其文学性是第一位的,科学性是第二位的,因此本质上是一部“文学游记”,我这些观点,主要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的解读与延伸,对深入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放在文本性质论争的百年历史中来看,也只是几声无韵的呐喊而已。而有意思的是,就在我写作这两篇文章时,无意中发现,从民国到解放后,中国出版了多部文学史著作,只有郑振铎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徐霞客游记》,他认为《游记》“无一语向壁虚造,殆为古今来最忠实、最科学的记游之作;而文笔亦清峭出俗,不求工而自工。”全文才七十多字,而且还强调了其为“科学的记游之作”。其余的文学史著作均对《游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只字未提。此事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觉得,这不是文学史家的疏忽,而是反映了文学史家们对游记的文本性质不同的理解问题。他们肯定也注意到了近百年来,围绕《徐霞客游记》种种争论的意见,他们显然不会同意丁文江先生把《游记》纯粹地定性为科学著作,但他们也不认为《游记》是纯粹的文学著作,而文学史是纯文学著作的集编,因此,不把《徐霞客游记》编入中国文学史,在他们看来,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
这一发现,对我触动很大,我想,近百年来对《游记》文本性质的探讨,主要是在传统的文本性质的范畴中争论。原来争论的四种意见,其实各有各的道理,但文学是发展的,文本的性质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变化。就拿游记来说,其实在汉以前,并不是单独的一种文体,人们都把它归入“记”或“杂记”中,到了魏晋南北朝才开始有正式的游记。但是,即使从魏晋开始游记正式诞生并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但其中不少游记仍然不具有文学性,有的只是一般出行的记载。因此,《辞海》包括《辞源》,开始都没有收录“游记”这一词条,一直到1979年版的《辞海》中才正式出现“游记”的词条,并指出它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以轻快的笔调,生动的描写,记述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加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对照这一定义,《徐霞客游记》毫无疑问可以算作文学游记,特别是前十七篇《名山游记》完全符合这一定义的要求。但是后边从《浙游日记》开始的整个《西游记》,就明显突破了这一定义的范畴,文中出现了大量的科学考察的内容,丁文江先生也据此认定其为科学著作。仅管《辞海》中对游记作了定义,但并不能解决近百年来,历史上对《徐霞客游记》定性的认识上的分歧。因此我想,关于《徐霞客游记》的文本性质的争论,之所以不能取得统一的意见,并不是参与讨论者的意见有错误,而是《游记》著作的本身的超前性,和讨论者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从而引出的认知上的分歧。徐霞客许多科学上的发现,是在他逝世后许多年,甚至数百年才被我们从新的科学高度加以确认。那么,在当今各科文学样式不断变革,新的文学流派不断涌现的时代,对《游记》文本性质的认识,难道不能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突破传统的框架,作出新的解读,新的探索?也许,从这里可以打开一扇在新时代里研究徐学文本性质光明的窗户!
二
就在我纠结于《徐霞客游记》文本性质的时候,意外地读到了鲁枢元先生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这引起了我深深的震憾,也使我在长期的困顿中解脱了出来,仿佛看到了解开《游记》文本性质的一线曙光。
鲁枢元先生,是苏州大学的教授,他长期从事文学跨界研究。他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2014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在这本书中,对陶渊明的诗歌,从歌颂自然的角度,站在现今时代的立足点上,作出了切合当今时代的全新的审视与评价。他认为“陶渊明的文学魅力,源于‘自然’的魅力,陶渊明的伟大,在予他与‘自然’的天然结盟;陶渊明的命运也因此与自然的遭际息息相关。”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是个元问题”,任何一个作家都是绕不开的,而陶渊明正是抓住了这个“元问题”,他的诗歌才真正具有了无限的生命力。他这样总结说:“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传世的作品并不多,为什么却在灿若星河的中国文学史中获得崇高地位,被赞誉为‘千古一人’的伟大诗人”,正是因为他为‘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提交了一份独具特色的‘答案’。我十分赞同鲁枢元先生的观点,陶渊明如此,我认为徐霞客也是如此。《徐霞客游记》之所以伟大,恰恰是徐霞客也抓住了“人与自然”的元问题。徐霞客的一生几乎都在和自然打交道,他寄身自然,观察自然,反映自然,几十年如一日,他的《游记》的价值,也正是来源于他最真实地记载并反映了自然,是自然给了他《游记》无限的生命力。
然而,我又纠结,因为陶渊明写的是诗,徐霞客写的是《游记》,是散文,两者毕竟有差异,怎么在自然文学这座桥梁上把诗和散文联结起来呢?出乎意料的是鲁枢元先生在这部优秀的著作中,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陶渊明与梭罗:在诗意中营造自然与自由的梦幻》一节专论中,把英国著名的自然文学家梭罗与陶渊明联结到了一起,并作了比较论述。他指出,梭罗与陶渊明相似的地方至少有五点:一是拒斥现行社会体制,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文明进步”的怀疑。作者认为,“陶渊明、梭罗反体制倾向无异包含着时代文明总体的审视和批判,这对于一种社会体制的健全发展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二是退避山野,返身农耕,在自然中寻求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支撑。作者认为,陶渊明与梭罗虽然同样是“退归原野”,但梭罗的“退”与“返”甚至更为决绝。他“似乎已经感悟到‘与天合其德’、把自己同化于自然之中,才是生命中最有意义、最美好的事。”三是持守清贫,以清贫维护生命的本真、生存的自由、灵魂的纯洁。作者认为陶渊明和梭罗都是“独立不羁”,以清贫为乐的典型,他们“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有不过”。四是崇尚精神自由,自做精神主宰,善于以生命内宇宙的充实替补对外部物质世界的索取;为了更高理想,不惮于超越现实营造空中楼阁。这里的“空中楼阁”,是梭罗提出来的,这是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作者认为,这和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是“他们在诗意栖居中营造的一个关于人类社会自然整全的梦幻,都不过是他们凭借自己的艺术想象对现实社会存在的一次诗意的超越。”但这种追求是美的,崇高的,是一种理想的体现。五是他们在各自民族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作者认为,“置身于不同时空、不同种族的陶渊明与梭罗,他们都在‘种豆’、‘锄草’的时代收获了文学上的庄稼。他们种下的不仅仅是豆子、黄豆或豌豆,同时也种下了他们各自的德行、乐趣、情感、理想,因而他们也收获了散文,收获了诗歌。”鲁枢元先生这些精当的阐释,使我从诗与散文的文体上的局限中解脱了出来,因为我知道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徐霞客游记》一样,都是散文著作,而且使我从一个与原来完全不同的视角,对徐霞客及其《游记》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我反复思考,深深感到,在上述五个方面徐霞客与陶渊明、梭罗有高度的相似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其当代意义愈加突出。徐霞客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他与陶渊明、梭罗一样,“拒斥现行社会制度,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终身寄情于山水之间,被后世称之为“游圣”。陶渊明是从四十岁以后才回归田野,到他去世,前后才二十多年;梭罗则更短,他三十八岁来到瓦尔登湖,四十四岁就病逝,前后才六年多。而徐霞客从二十四岁起一直到五十四岁,前后三十多年,游历了中国的二十一个省、市,写下了百余万字的游记,这是陶渊明和梭罗无法比拟的。陶渊明和梭罗退避山野,返身农耕,并能持守清贫,以清贫维护生命的本真,乃至灵魂的纯洁。徐霞客同样如此,一生寄身山野,他在西游中,特别是湘江遇盗之后,所带盘缠全被强盗抢去,但他依然不改志向,继续西行,几次卖掉衣衫。靠着朋友的帮助,才最终完成了他西游的意愿。因此有人评价说,徐霞客的西游是“穷游”,这难道不正是徐霞客“以清贫维护生命本真”的具体表现?因此,如果说,陶渊明与梭罗能“崇尚精神自由,自做精神主宰,善于以生命内宇宙的充实替补对外部物质世界的索取”,那么徐霞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至于身后的事迹被记载入文学史,这一点,正如我前文所说,中国的文学史除了郑振铎外,其余的几乎都没有记载,这一点和陶渊明、梭罗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明徐霞客贡献就不如陶渊明和梭罗,否则,为什么现今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称之谓“徐学”,而且研究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被称之为“千古一人”的陶渊明呢?这里恰恰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只是停留在传统的认知范围内对徐霞客及其《游记》进行研究并作出评价,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像鲁枢元先生一样,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跳出传统游记的框架,从自然文学的角度着眼,重新认识,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基本特点及其在新时代的伟大意义,我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真正与新时代接轨,对徐霞客及其《游记》有个正确的评价,才能把徐学研究推上一个与新世界同步前进的水平!
三
美国的自然文学,是享誉世界的,梭罗只是美国自然文学的一个杰出的代表,因此只有把徐霞客及其《游记》放到美国的自然文学一起考察、比较,才能真正了解把《徐霞客游记》定义为自然文学的重要依据及其重大意义。
美国的自然文学进入中国的主要推荐者是著名的学者程虹。她在《寻归荒野》一书中系统的介绍了美国从17世纪到当今的诸多自然文学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她在《寻归荒野》的开篇《美国自然文学的概念》中,对自然文学做了定义。她认为:“从形式上来看,自然文学属于非小说的散文体,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言之,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依据程虹先生对自然文学的定义来看,《徐霞客游记》无不契合这些定义的要点。《徐霞客游记》的形式,通篇都是“排日纪事”的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徐霞客以足迹为线索,记载了途中所见,思索的重点正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游记》通篇无一处虚构,都是以“写实的方式”反映了作者对自然环境的独特的“身体和精神的体验”。因此可以说,《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古代自然文学的杰出代表。
程虹先生还指出:自然文学主要特征有三:1、土地伦理(Land ethic)的形式。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呼唤人们关爱土地并从荒野中寻求精神价值。2、强调地域感(sense of place)。如果说种族、阶层和性别曾是文学上的热门话题,那么,现在的生存地域,也应当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3、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这里程虹先生从内容到形式上,对自然文学作出了具体的特征性的解读。《徐霞客游记》在这三方面无不具有相应的特征。
首先,看看“土地伦理”的问题。土地伦理,是美国著名的自然文学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他的《沙乡年鉴》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土地伦理的范畴包含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以及大地上存在的一切。土地伦理观就是让人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放弃征服者的角色,对每一个伦理范畴中的成员给予自然平等的地位,呼唤人们关怀土地,并从中寻求崇高的精神价值,徐霞客和利奥波德虽然出生的时代不同,尽管这样,徐霞客和利奥波德一样,对于“土地伦理范畴中的成员”,如大地、水、植物和动物等都看作是“自然平等的地位”,是朋友和亲人的关系。因此,陈函辉送徐霞客诗中写道:(徐霞客)“寻山如访友,远游如玩身”。这充分说明,徐霞客始终把山水草木当做朋友看待,而远游到群山、荒野之中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这种观念,早早出现在明朝末年,真是十分了不起。《徐霞客游记》中,记载徐霞客对自然山水崇敬的描写,几乎俯拾皆是。例如《淅游日记》中,记载徐霞客来到金星峰,在夕阳西下,面对江面无限美景时写道:“夕阳已坠,皓魄继辉,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另一是静闻)形影俱异,迴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这里不仅写出了绿水青山,无与伦比之美,更写出了徐霞客与自然万物(包括“山精怪兽”)和谐相处之乐,这岂不是徐霞客与大自然平等相处的真实写照?正因为这样,明末清初的大儒黄道周的夫人蔡玉卿读了《游记》无限感慨,在诗中对徐霞客称颂道:“徵君探遍幽玄绩,更侣山灵护绝纵。”她称赞徐霞客一生贡献给大山绿地,而且与山地的神灵也能和谐相处。因此,我认为,尽管徐霞客早于利奥波德三百多年,当然他也不可能看到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观”,但他对自然的尊崇,对动植物的爱护,这不仅在明末清初是一种极为先进的理念,而且和三百年后利奥波德的观念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我们看看“强调地域感”的问题。程虹先生认为自然文学要跳出“种族、阶层和性别”等文学上的热门话题的圈子,应该把“现在的生存地域”赋予重要地位。这确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不仅仅是题材的选取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否彰显并保持自然文学的特色的关键问题。程虹先生在《寻归荒野》的“增订版序”中写道:“多年的研究与经历使我感到,荒野不仅是实体的自然,也是自然的心境,或心境中的自然。”程虹先生这一体会十分重要,这不仅是她个人对自然文学的一种深刻地理解,而且她在《寻归荒野》一书中正是按照这一特定的标尺,对美国的自然文学著作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和阐释。徐霞客呢,他的代表作是《游记》,他在《游记》中地域感同样特别强烈,随着他足迹所及,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面对这些祖国的秀山胜水。真实记下了当时的时代风貌,描绘了当时中国实体的自然,表达了他“自然的心境,或心境中的自然”。例如,他先后两次游黄山,他用饱醮深厚感情的笔触对黄山的奇石、怪松、云海、温泉一一进行了描摹,从而使读者对“黄山四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如,他五十一岁开始西游,从浙游作为起点,到五十四岁于鸡足山病足为止,这前后四、五年中,他经过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最后到达云贵高原,后人把这称为“万里遐征”,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因为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更重要的是,他边行边记的几十万字的日记,写出了当时中国富有各地不同地域特征山水风貌和社会风情。不妨举两个例子来佐证一下。《浙游日记》中,徐霞客来到杭州飞来峰,他用了一段优美的笔触记载了当时眼前的景致:“……至此峰尽骨露,石皆嵌空玲珑,骈列三洞。洞俱透漏穿错,不作深杳之状。……山间石爽,毫无声闻之溷,若山洗其骨,而天洗其容者。余遍历其下,复扪其巅,洞顶灵石攒空,怪树博影,跨坐其上,不减群玉山头也。”短短的一段描写,就把江浙山水玲珑剔透的地域特色,尽显于读者面前。徐霞客来到云南,发现云南的山水与江浙一带不同,这里多高山险峰,悬崖峭壁,于是运用了与江浙一带不同的笔触记下了途中所见。《滇游日记五》中,他来到华首门,他这样写道:“二里,出循崖正道,过八功德水,于是崖路愈遍仄,线底缘嵌绝壁上,仰眺只觉崇崇隆隆而不见共顶,下瞰只觉窅窅冥冥而莫晰其根,如悬一幅万仞苍崖图,而缀身其间,不辨身在何际也。”徐霞客不仅在《游记》中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华首门一带山水风光的独特性,而且创作了《华首重门》的诗歌,写出了自己对这一景点难以忘怀的强烈的“地域感”。因此,可以说,徐霞客是中国古代“地域感”最强烈的作家之一,整部《游记》是他旅游中表达他不同地域感的最有力的实证!
再次,关于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的问题。程虹先生对美国的自然文学的文学形式和语言,在《美国自然文学的理念与特点》一节作了具体的阐述。她认为,美国的自然文学之所以取得如此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写作主题上的突破。她说:(美国)“自然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文学与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以及传统文学中的战争、爱情与死亡那些经久不衰的话题,大胆地将目光转向自然,把探索与描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视为文学的领域并作为写作的主题。”我认为程虹先生在这里抓住了自然文学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关键是人类要突破“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将目光转向自然”,这是独特的文学形式形成的前提。徐霞客就是这样做了,史夏隆说徐霞客终身寄身自然,“驰鹜数万里,踯躅三十年。”丽江《鸡山志》说徐霞客是“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这在古代中国,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现存的六十万字的《游记》,也充分说明了,他已突破了“以人类中心的传统观念”,真正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也正是《游记》的主题所在。程虹先生认为:“自然文学的文体和风格,使文学走出了‘象牙塔’,因为自然文学作家访问的对象,如梭罗所说:‘不是一些学者,而是某些树木’。在自然文学作品中留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笔记,而且还有他们的足迹。”程虹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自然文学有其内容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文体和风格的独特性。《徐霞客游记》恰恰是这样,由于通篇作品论述的是徐霞客寄身山水的伟大过程,因此,在这部《游记》中,不仅留下的是徐霞客的“笔迹”,更留下了他的“足迹”,这就决定了这部作品自然文学的特性,也即是具备了自然文学的文体和风格,虽然,在徐霞客的时代,还没有明确的自然文学的提法,但那时有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家,也已意识到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如钱谦益就是这样。他在《徐霞客传》中,带着对徐霞客崇敬的心情,写道:“居平未尝鞶悦为古文辞,行游约数百里,就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画,虽才笔之士,无以加也。”这里钱谦益实际上指出了《游记》为对大自然考察的记实文学,是徐霞客寄身自然、探索自然,终身与自然为伍的产物,于是他把《游记》称之为“千古奇书”。因此,可以说。《游记》是中国古代使“文学走出象牙塔的一部杰出的自然文学”的代表作,它比美国的自然文学更早,在世界文学史上永远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这里,还是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自然文学的语言问题。程虹先生指出,美国的自然文学在普遍具备强烈的“地域感”的同时,他们“这种与土地接壤的文学,在语言方面也不同凡响,它使用的是与之相应的‘褐色的语言’,那种朴实如泥土、清新如露水的鲜活的语言。”“褐色的语言“,程虹先生这一概括,既形象又生动,是最准确的说出了美国自然文学的语言特色。那么徐霞客呢?我认为把他的《游记》作为自然文学来考察,和美国自然文学的语言特色有着明显的共性,我在多年前,就提出了《徐霞客游记》的语言是有独特的色彩的,它的语言是“本色的语言”(见《<徐霞客游记>的本色语言刍议》)而且指出,他的这种本色语言是继承了“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本色独造语”的精华,在此基础上改造制作而来。并且把徐霞客在《游记》中的语言特点归结为四个方面,特别是强调了“质朴自然,精准鲜活”和“情真语直,尽显本色”的特点。尽管当时我在写作时还未看到程虹先生的《寻归荒野》一书,但意外地不约而同的一样强调了语言运用必须“朴实”和“鲜活”的特点,这充分说明徐霞客的语言已具备了自然文学所要求的“朴实如泥土、清新如露水”的特色。虽然,语言的问题比较复杂,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徐霞客的自然文学语言,带着中国特色,它与美国、欧洲等国家的自然文学语言有着共性,但又有着中国的独特的个性,因此它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必将永远在世界文坛上熠熠闪光。
四
把《游记》定性为自然文学,我认为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是使近百年来对《游记》文本性质的争论,有了个贴近时代的结论。我在文章开头,简略的介绍了近百年来关于《游记》文本性质争论的各种意见,其实,这一争论的焦点,是关于《游记》是科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之争。后来为了使争论双方取得统一,从毛泽东同志开始,以及《游记》整理者褚绍唐、吴应寿,还有朱惠荣先生,干脆把《游记》定性为既是科学著作(作品),又是文学著作(作品),这样暂时取得了统一,但是,正如我前边介绍争论情况时所说的那样,其实对《游记》文本的认识,没有取得统一。但是,不管怎样,对《游记》文本性质的认识,确实是在逐渐深化,尤其是丁文江先生提出了“科学著作”的论断后,使大家认识到《游记》不同于中国古代一般的写景记游的文章,它记载了徐霞客在游历中的大量科学考察的内容。因此,这一争论虽然没有在《游记》文本性质上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但通过争论不仅吸引了广大读者对《游记》的关注,扩大了《游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使《游记》文本性质的讨论得以不断深化,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这次,把《游记》定性为自然文学,正是对《游记》文本性质的认识,在百年争论的基础上,一次圆满的总结,也是新时代文本性质不断被变革,不断被创新的结果。作为自然文学,它是集科学性与文学性为一体的。长期争论的《游记》是科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正是在自然文学这一文体上得到了统一,因此,我认为,把《游记》定性为自然文学,是对《游记》贴近时代的一种新的认识,也是符合《游记》自身特点的结论。二是把《游记》定性为自然文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正确认知,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物。徐霞客的游记写于明朝末年,正式编撰出版已是清朝初年,因此,即使把它定性为自然文学,它也是带着明朝那个时代特点的中国古代的自然文学作品。但是这一典例启迪我们思考:徐霞客的《游记》可以跨越时代,把它定性为自然文学,那么,中国古代浩似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没有与徐霞客的《游记》类同作品呢?也就是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的其他自然文学作品呢?我认为肯定有,这里不去探考鲁枢元先生肯定的以诗歌为代表的陶渊明一类的作品,只从与徐霞客一样写游记的人为对象,进行考察,我认为柳宗元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个。柳宗元是中国中唐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参与政治改革失败后的贬谪生活,这时候他深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与人情淡薄,因此开始走向自然,尤其在他贬谪到柳州和永州后,他更是沉醉于自然之中,写出了著名的《永州八记》。而这《永州八记》,我认为是中唐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典型的自然文学著作。下边以《永州八记》之四的《小石潭记》为例。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写出了小石潭的方位及其总体形象:“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金石以为底,迎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嶼,为堪,为岩。青树翠幔,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极为简洁地写出了小石潭的形象美。接着写了鱼游澄水中的形态:“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里不仅写出了鱼的静态动态,而且写出了水的清冽。用“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写出了诗人在潭边远望所见。再接着柳宗元写了小石潭周围的气氛:“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因环境过于清幽,“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最后交待了同游之人,这样的一篇记游文章,虽然比较短小,但参照已经定性的《游记》,谁能说它不是自然文学呢?因此,我认为中国的自然文学,实质上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绝不仅仅只有徐霞客的《游记》一书,而是有不少自然文学的珍品客观存在着,值得我们突破传统的视野好好地去发掘、研究。三是自然文学是当今世界的新的文学潮流之一,把《游记》定性为自然文学,有利于跨越时代,把它推向世界。当今的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着,文学界同样如此,自然文学的兴起,正是文学艺术日趋多元化的一个标志,它冲破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思维,为中国文学迈向世界,同世界文学接轨,打开了一扇大门。前边,我把《游记》从自然文学的角度,与美国的自然文学做了比较,突出了其共性的一面,实际上,《游记》作为中国古代自然文学的杰出代表,还有着自身的许多特色,这种“中国特色”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另外,自然文学在欧洲,在俄罗斯(前苏联)也以自己各个国家的鲜明的地域特色存在着,作为中国古代的《游记》,与这些国家的自然文学又有哪些共性,哪些差异,也值得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我深深的感到,让《游记》以自然文学的面貌进入世界文坛,其意义特别深远。鲁枢元先生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语重心长的指出:“关于陶渊明的当下解读,或许会为‘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提供一份东方式的解答,从而为当代人走出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寻求一线生路。”我深深感到,揭开《游记》自然文学的真面目,并让它跨越时代,融入世界,绝不仅仅是为了《游记》在世界文坛上争得一席之位,而是因为《游记》在“人与自然”的这一元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比陶渊明更多的更为具体的可供参考的答案,而这也是《游记》跨入世界文坛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把《游记》定性为自然文学,在徐学研究的领域中是一种新的探索,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但是,我深信,正因为它“新”,它与时代同步,它同世界接轨,也许最美丽的风景就在这未来的天地中。
2020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