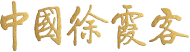

探寻建文遗迹,徐霞客西游不可言说的秘密
畅朝晖
徐霞客,世界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博物学家,被尊称为“游圣”。他二十二岁青春年少之时开始出门游历,三十多年间东游普陀,往北到了山西、河北、北京一带,向南抵达福建、广东,西南远至广西、云南和贵州,足迹遍及大半中国。他将游历的所见、见闻、所得,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下来,后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徐霞客西游广西、云贵等地,不仅仅是赏自然美景、探山川形胜,找寻建文皇帝遗迹,是他游历当中一个不可言说、不可明说的秘密,因为当时人们“犹讳言之也”。
一、建文失帝号,历史存迷案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在他还是皇太孙的时候,他就开始参与朝政,《明史》中记载:“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礼记》)正象他的号一样,建文帝以文建国,重礼尚德。《明史》其本纪赞曰:“践祚之初,亲贤好学。”但随后发生了靖难之役,叔父燕王朱棣起兵,双方陆陆续续打了四年,最终,朱棣取得了胜利。“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有明一代,甚至到清初,江南一带百姓始终怀念建文帝。一百多年后的弘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之心若此者矣。”朱棣大军到的时候,老百姓“哭声震天”,建文的属下战死的战死,自杀的自杀,归隐的归隐。最后概括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亡国之君,有像建文皇帝这样得民心的。
建文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中国四大历史迷案之一。《明史》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也就是说,建文皇帝可能从地道中逃走了,而且很可能削发为僧当了和尚。民间也一直流传着建文皇帝往来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一带的故事和遗迹。
徐霞客也在游记中写道,“帝遁后,先入蜀,未几,入滇,尝往来浙东、天台、广西、云贵诸寺中。”(《滇游日记》)云南武定县的狮子山上的“龙凤柏”传说是建文帝亲手种植的,山上还有供奉他塑像的祠堂,大门上有一幅对联:“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对于朱允炆、朱棣颇多感慨。徐霞客曾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十一日抵达武定,停留数日,访问狮子山,可惜这段时间的日记已散失。想来,徐霞客是想以亲身实践揭秘、探秘的。
二、桂黔留遗迹,霞客细探寻
徐霞客游历广西横县的时候,在《粤西游日记二》中写道,横州(今横县)城“南十五里曰宝华,在城东南隅。宝华山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其寺西向,寺门颇整,题额曰‘万山第一’。字甚古劲,初望之,余忆为建文君旧题,及趋视之,乃万历末年里人施怡所立。盖施怡建门而新其额,第书己名而并设建文之迹。后询之僧,而知果建文手迹也。余谓‘宜表章之。’僧‘唯唯。’”寺门“万山第一”的题额,霞客判断是建文手迹,后从寺中僧人那里得到证实。徐霞客接着探访,继续深入“寺后冈上,见积砖累累。还问之,僧曰:‘此里人杨姓者,将建建文帝庙,故庀(pǐ,备具)材以待耳。’吁!施怡最新而掩其迹,此人追远而创其祠,里阈之间,知愚之相去何霄壤哉!”霞客在寺后的山岗上,看到堆积着许多砖块,询问僧人后得知,是一位姓杨的当地人准备修建建文帝庙。徐霞客对此感叹道:施怡翻新寺门掩盖建文帝遗迹,杨姓乡民追念历史,准备建建文帝祠庙,同一乡里之间,智者和愚者的差距真是天地之别啊!此后,徐霞客登舟向南宁方向进发,“舟转北行,又十里抵陈步江(今沙坪河)。在江南岸,通小舟。内有陈步江寺,亦建文君所栖。”这是关于建文帝的又一记述。
游历贵州黔南州长顺县白云山,霞客看到、听到了很多有关建文的遗迹和传说故事。《徐霞客游记》中写到贵州的部分有三十二万字,其中考证建文帝在长顺白云山出家修行的记述就有三千二百余字,占到了十分之一,比较而言着墨最多。
其一,太子桥。“止贵州(指贵州布政司和宣慰司治所,在今贵阳市区),寓吴慎所家。晨饮于吴,遂出司南门,度西溪桥,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黔游日记一》)这里,徐霞客对“太子桥”的名称提出了质疑,指出建文帝实为“太孙”(明太祖朱元璋病逝,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依祖父遗诏即皇帝位,为惠帝,年号建文)而非“太子”,体现了其严谨的考证态度。
其二,巨杉。“一里,逾其脊,是为永丰庄北岭,即白云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东西坞。有村在南山下,与北岭对,是为永丰庄。从坞中东向行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转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树深丛,石级迤邐。有巨杉二株,夹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
其三,白云寺。“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白云寺以建文帝为开山之祖,因建文帝看到山顶白云而登山所以命名。
其四,跪勺泉。“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双金鲤出没云。”“跪勺泉”景观现在被称为“跪井”,由于位置特殊,人难以站立取水,只有俯身下跪,才能舀起井中泉水。
第五,流米洞。“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傍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
第六,潜龙胜迹阁。“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徐霞客对建文帝可能的遁迹之地与民间传说,没有盲目听信,采取的是一种严谨审慎的态度。“皆神其迹者所托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霞客的记述既保留民间传说,又对其真实性持有一定的怀疑。
第七,唐帽山。“西望三峰攒列,外又有峰绕之,心以为异……其北崖中断,忽露顶上之峰,盘穹矗竖,是为唐帽山。盖即前望三峰,至是又转形变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自然(僧人名)言建文君先驻唐帽,后驻白云。《志》言其处可以避兵,亦幽閟之区矣。”
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徐霞客还几次提及南京井、南京僧和北京僧。“逾而北,开坪甚敞,皆层篁耸木,亏蔽日月,列径分区,结静庐数处。而南京井当其中,石脊平伏岭头,中裂一隙,南北横不及三尺,东西阔约五尺,深尺许,南北通窍不可测;停水其间,清冽异常,而不减不溢;静室僧置瓢勺之。”至于南京井的得名,霞客解释道,“以其侧有南京僧结庐住静,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犹仍其旧也。”“是日下午,抵白云庵。主僧自然供餐后,即导余登潜龙阁,憩流米洞。命阁中僧导余北逾脊,观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第二天,霞客“欲往探龙潭”,见龙潭“水中深不可测,而南透穴弥深……直西南透为南京井,东南透为跪勺泉者也。”徐霞客正是凭借着这种孜孜以求、朝夕不倦的精气神,为我们寻到了“跪勺泉”和“南京井”的源头活水。此后,霞客“循旧径返”,“还逾潜龙阁”。
围绕“潜龙阁”“流米洞”“跪勺泉”,霞客的笔触多次提到“南京井”,还有“南京僧”和“北京僧”。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定金陵为国都,称南京;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帝宝座,将北平改称北京。联系徐霞客这段日记中建文遗迹颇为详细的点点滴滴,“南京井”“南京僧”“北京僧”,不由地让人浮想联翩,这只是平常文字,还是另有深意,春秋笔法?
三、理念感同身,文字遗后人
可以说,徐霞客西游探寻建文皇帝遗迹,收获颇丰,不虚此行。徐霞客亲身的探访、如实的记录,为研究建文帝下落提供了重要的实地考察资料,这些文字具有极其重要的佐证意义和历史价值。
霞客称建文为“君”,甚至直接用“帝”字,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读出他对建文的尊重以及深深的同情与怀念。
霞客的家乡江阴,与曾经的都城南京近在咫尺,史实与传说相交织的建文事迹不可能不深深影响到霞客。尤其身处明末乱世,便更加怀念建文帝以文治天下的功德。霞客会不会这样设想,如果没有靖难之役,明朝是否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我想,建文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思想,应该是与霞客心目中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更为接近,这是一种理念的认同。霞客追寻建文遗迹,更是对心中理想的追寻。
尊敬的《徐学研究》编辑老师:
作者系 上海松江徐霞客文化中心会员